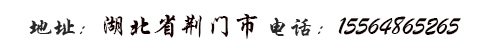那时候的哈尔滨,百年飘香的俄罗斯大面包
| 多年白癜风能治好吗 http://m.39.net/pf/a_4684514.html光阴匆匆而过,那些最美的日子,走得太急,太急。岁月爬上了额头,往事不再回来。每一段留不住的岁月,都是永远回不去的曾经,是难以忘怀的时光……无论你在何处、在外闯荡多年,即使天天山珍海味,但对家乡的味道难以忘怀,那味道流淌着那些失去的无人问津的历史。那老味道多像一颗颗芳香多彩的糖块,甜甜的在回味中融化在记忆升华里,更像是一杯清茶,带着淡淡的清香和苦涩,让我们慢慢去回味。面包是俄罗斯人最常见的主食。据说早年在俄罗斯,每个村庄一般只有一个面包炉,每个家庭都是轮流到这个面包炉烤面包的,每次都要多烤一些回来,储存在家中吃。为了多储存,所以他们制作的面包非常大,质地也比较硬,吃的时候要切成片片。久而久之,这种乡村面包的制作形成了特有的技艺和风俗。年俄国人在中国修建中东铁路,俄罗斯人大量涌进哈尔滨。为了适应他们的口味,俄罗斯商人便把大列巴的制作工艺引到了哈尔滨,前店后厂生产大列巴,这一烤就是一百多年。面包是俄国人的主食,大家知道,在西餐厅用餐的时候,正餐前就会上面包,作为在餐厅里食用的第一款食物,面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受俄罗斯影响颇深的哈尔滨人,也酷爱吃面包。俄式面包传统的加工方法是以啤酒花做引子发酵,这是与所有面包不同的地方。它是经过四次发酵后加入适量的盐用木柈烤制而成,烘烤一定要用木拌子,还要喷水。在刚出炉后的大面包,外皮焦脆,内瓤松软,香味独特,别提有多好吃了。大面包是圆形,若论个头大小堪称面包之冠。早年大列巴的个头要比现在大一圈儿,差不多就像洗脸盆那么大,现在的要“袖珍”很多了,像艺术家戴的那种贝雷帽。俄式大面包是哈尔滨一个特色,慕名而来的总要买一个带回去,所以这队伍中常有不少外地人。有不少人,把大面包买回去后觉得不好吃,吃不惯。其实是吃法不得要领。面包不能像馒头一样,拿起来就咬,需要涂奶油、果酱才行。这正像中国人吃饺子,总要蘸点醋是一个道理。一般可以把大列巴切成片,烘热后抹上果酱,夹上奶酪,或者抹上黄油、鱼籽酱,最好与香肠一起吃,或者做点苏波汤与之相配,这样味道就更纯正。还有一种梭子形的列巴----叫塞克,五六十年代,一毛四钱一个,学生开运动会或郊游带上一两个塞克、一根红肠、一瓶汽水,就是很不错的饭食了。那个时候,哈尔滨的俄式住宅家家离不开烤炉。这种砖砌的烤炉,就可用以烤制列巴。在中央大街西侧的一条街道上,是哈尔滨最早的面包房之一它见证着哈尔滨面包的起源,相信每一个哈尔滨人都曾经在它的门前走过。然而它也像哈尔滨众多历史建筑一样,几乎已经被掩埋在这座城市当中了,完全看不出当年的历史印记。每当走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上,总是会看到排着长长的队,十米开外就能闻到那股子老式面包香。因为上个世纪初哈尔滨这里曾经有一半以上的居民是外侨所以这里成为中国最早将面包作为主食的城市之一。原梅金面包房(现在大安街30号,—?)梅金面包房是犹太人梅金兄弟上世纪初在哈开办的,他们用机械制作面包,成为哈市规模最大、生产水平最高的面包厂,也将面包的技术带到了哈尔滨。不过仅凭外观已经很难找到当年历史的印记了,整栋楼都湮没于商业区中,只有楼上标注的“年”字样,显示出它悠久的历史。如今我们只能依靠想像来还原它当年的样子:冬日的早上,天际刚发亮,哈尔滨百年老街中央大街上就弥漫着阵阵的面包香,那是烘烤的面包散发出的古老而独特的味道。厂房大门打开,运送刚出炉新鲜面包的马车鱼贯而出,这些新鲜面包就将被运送到城市的各个地方。而面包房附近等待购买的市民和游客早已经排起了长队,哈尔滨的一天就在面包的香气之中开始了……小时候我家斜对着烤面包的小作坊,都叫它列巴炉。在安松街与安顺街街口与我父亲的木匠铺为邻,每天清晨天没亮那厚重的、奇香无比,充满诱惑力的烤列巴味道在周围几条街道上自由自在游荡着。打开窗户,浓浓的香味闯了进来,朦胧中它钻进我的鼻子溜进我五脏六腑顿时睡意全无。这美妙之味催我起床陪伴我一路上学。列巴炉五十米之外是安静小学,清晨朗朗书声与阵阵列巴香味在教室共存,配合的那么和谐,好像世界都是香的,那是快乐无比的味道,是让我对未来充满美妙幻想的味道,那种味道用语言是描述不出来的。不像安静街头安广街上第五中学的中学生们每天与安升街与安静街口的酱菜厂大家叫它酱园子的豆瓣酱和酱油味道为伴,味道虽不及列巴香,但它实实在在,它不会引起美妙的幻想只赋予现实。从新阳路顺着安升街慢行,味道在迅速变化着,先是酱园子的酱香味接着是隔壁冰棍厂的菠萝香精味,再走二步便是龙江鞋厂的皮革和熬胶的臭味。只有列巴炉烤的列巴一年四季保持着真实的原味没有节假日的变化。那时做列巴只用面粉、水、咸盐、老面和列巴花,只用桦木和柞木柈子明火烤制。最初制作大列巴的面包师,多是闯关东的山东人,他们工作吃苦做事认真,加之当时大列巴市场行情好,收入十分可观。当时还有句顺口溜:“上有天堂,下有列巴郎。大姑娘行三辈子好,才能嫁给列巴郎。”我有个远方堂哥叫“豪”五十年代在山东家吃不饱,胃还不好,瘦的皮包骨,来哈尔滨梦想当农民工学木匠。木匠们看他太瘦干不了重活便介绍去了隔壁的列巴炉当临时工,对他说喝点列巴花泡的水治胃病….那东西还真灵,没几年“豪”的胃病好了脸也红润了,只是还是那么瘦。堂哥人好,心灵手巧,干活从不偷懒。其实做列巴的活很辛苦不比木匠干活轻。趴在窗户看他干活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硕大面团面在那瘦小身体面前前后左右揉搓着,上下拍打着,烤炉里暗红的炭火烤的列巴冒着灰色白色的烟汽,烤他满脸通红汗水湿透了工作服。“豪”很幸福。他终于成为一名做列巴的工人。和其它师傅一样畅快的大口喝着用烤糊发黑的列巴渣和列巴花自制的格瓦斯。“豪”成为列巴炉数一数二的技术骨干,他烤的列巴小有名气。(退休后“豪”回山东老家,在莱州城里开了自己的面包房买卖很是兴隆)六十年代初我们国家遇到了困难,外侨老毛子买列巴也要拿侨民证定量供应,安静街十号住着一位孤独的犹太老头,满脸大胡子很像马克思,他一条老狗天天坐在他家的门口陪着他一动不动。每天上午老头准时到安宁街福发源食杂店买他的那份列巴。圆桌的一碟盐面、一点砂糖,一个瓶子里的干列巴花。旁边地上有个木桶,装着他每天剩下的咬不动的列巴皮加列巴花和砂糖泡的酸溜溜自制格瓦斯,这就是老头每天的三顿饭。中国邻居们看老头可怜,夏天送一碗“苏伯汤”(大头菜西红柿汤)冬天送一碗冒着热气的“山东咖啡”(高粱面粥)几乎天天不断。多么善良的哈尔滨人!可怜的犹太老头只是微微点点头从不说话但眼睛里充满了感激和无奈。以前犹太老头家的园子里种很多列巴花和樱桃树,后来都枯萎死了,人也死了。留下了满园子的野草和凋谢的列巴花。今天做面包有品种齐全的食品添加剂,电动搅拌机,带温控的电炉…列巴花过去这个唯一的“添加剂”人们已经忘记了。据说列巴花是欧洲人发现了这种植物具有独特的香味和防腐作用。后来德国的酿啤酒师和烤面包师们发现这种植物烤列巴、酿啤酒的妙用,是先用于烤面包还是用于酿啤酒已无从考证。在酿制啤酒要放一些叫啤酒花,做列巴放一些就叫列巴花其实是一种东西。一些无良商家,为了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迎合这些消费者的口味,在面包中加进了无数添加剂,有些甚至是有害致癌的,也使食品加工的传统工艺受到了毁灭性的冲击。也许有人说是新技术替代了落后的技术,但是替代可以,口味不能替代,因为口味是没有先进与落后的。面包与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一样,并不是花里胡哨的好,简单本真往往才是好的。创新不一定是进步,传统往往更值得珍惜。俄罗斯大面包就是一个面团,没有任何添加剂,只有盐和酵母,吃的就是面味;必须用木柈烤制,电烤的不行。实际上,无论俄罗斯,还是法棍或德国裸麦,丹麦的黑麦,哪一个国家的面包都是原味的,他们爱吃黑面包,甚至超过白面包。但这种原味并不适合每个中国人,一些吃惯了馒头和烧饼的国人,刘姥姥初进大观园,认为洋面包就得有洋味,洋味就应该是又松又白,香气四溢而且甜香如蜜。殊不知洋人恰恰不吃这种面包不面包,蛋糕不蛋糕,土不土洋不洋的东西。大列巴,历经百年仍旧满城飘香,已与这座城市密不可分,影响深远,成为哈尔滨多元文化遗留下的饮食遗产。大列巴、塞克、槽子面包、列巴圈等至今还是很多哈尔滨人家经常吃的食品。对于哈尔滨这个城市来讲,大面包早已超越了食品的概念,它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份记忆,一种像征,更是这个城市历史的见证和传承。儿时的味道再也闻不到了,变成永恒的回味。天翻地覆的巨变让那些熟悉俄罗斯的木板房、老校舍、老工厂、老邻居…在历史长河流逝的无影无踪,只能独自坐在沙发上,伴着一杯清茶慢慢回味。故乡曾予我一丝不经意的味道,我却记一生家乡的温暖、回味那些忘不掉的味道……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ijiuhuaa.com/pjhyc/8339.html
- 上一篇文章: BABSGAle其他艾尔
- 下一篇文章: 以前她总是挡着不让喝,现在她和我一起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