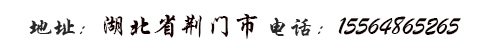如果你也想研究云雪花沙子和月亮
|
▼ 按:读小库的“14岁懂社会”系列丛书,引进自日本河出书房,是一套由日本各个领域的职人(比如律师、心脏外科医生、法医、动物饲养员、精神科医生、迪士尼员工、编剧……)专为14岁左右孩子写作的“人生指南”。编辑一重苜曾说:“我无数次地回望自己的十四岁,无数次地遗憾自己为什么没在十四岁时遇到它们。若遇到,不敢说人生会大不一样,但起码可以小不一样。”当然,不管几岁都不晚。这套书已经成为不仅是中学生,连年轻人甚至中年人都深有共鸣的读物。读小库在公号开启“14岁采访计划”,为大家介绍一些国内各个领域从事着自己喜欢工作、并且做得很棒的大人。他们14岁时有什么困惑,想做什么,又有哪些给14岁的孩子的建议呢?如果你身边有14岁左右,正为应试教育困惑的孩子,希望这些内容可以给他一点鼓励。第一期要介绍的,是我以为是天文学者,但自称是“天文学渣”的张超。我只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张超明年满40岁,从天文学系硕士毕业后,他先在《博物》杂志工作,之后又到了国家天文台的《中国国家天文》杂志。年4月的一席演讲,张超的主题是“尘与雪”。他穿着红色冲锋衣外套,拎着工具箱,自嘲“像是来送外卖的”。他在河北山头的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工作,那里有我国目前最大的光学望远镜。工作并没有想象得浪漫,是用望远镜对着天上的某个目标,“一张一张地拍摄,一拍就是半年的时间,其实很枯燥”。天文观测对于天气的要求非常非常高,雾霾、云彩、阴天、下雨、下雪,都会影响观测。碰上被影响,没办法观测的日子里,张超开始研究起了这些令人讨厌的云和霾,于是每一天都开始期待,会记录、观测到什么新的云,它叫什么名字,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他将拍摄到的种云整理记录成中国版的观云百科《云与大气现象》。不再满足于用相机拍摄云,他开始尝试用显微镜拍雪花。张超拍摄的北京的雪花。拍雪花是件看似浪漫,实则需要专业与忍耐的事情。需要学会在野外使用高倍显微镜,需要将相机和它连接,并且充分冷冻,人也需要忍受极低的气温。某年春节,大雪封山,交通和补给都切断了,张超就在观测站和同事们吃着过期饺子、拍着雪花过了年。雪花有着多个种类,每个种类出现的地区与伴随的天气环境都不一样。张超在东北拍摄的雪花,直径超过两个厘米。 因为世界上已知最大直径的雪花是三厘米,所以“还有值得盼望的”。我们很容易以为雪花就是六瓣的,但实际拍摄了才知道,雪花也有“糖三角”,也有四瓣的。也有十二瓣的。在天文台拍摄时,两片十二瓣的雪花从天而降,对张超来说,是“梦想成真”的时刻。而同时,他的袖子上沾上一颗毛茸茸的雪花——这也是目前已拍摄到的瓣数最多的雪花照片。 他也拍各个地方的沙子。在我们眼中全无区别的细小沙子,在他的镜头下,“有着浪漫的玫瑰色”。鸣沙山会叫的沙子,像一个个小的和田玉。福建沿海的沙,像“可口的小饼干”。冲绳的沙子,由一种海洋有孔虫形成的星砂,“像小星星一样”。冲绳的星砂。 张超也拍放大了一千倍的雾霾,被告知“看起来很恶心”,却还忍不住解释“其实不难受的,这些也挺美的嘛”。还拍儿子的尿尿,啤酒花,电池玩具的漏液……“即使是随处可见的生活,也有美的存在,它们都是有自己的故事的嘛。”学习真是太痛苦了!“我14岁的时候是想做微生物相关的。小学时候只知道模糊的喜欢不喜欢,但初中时觉得微生物很有意思,细菌、病毒、亚细胞,脑子里第一次冒出来‘想要成为什么’的念头,就是想做微生物相关的研究。”初中时,他就会去学校历史年代久远的墙上扒拉,寻找各种各样的植物——不是花也不是草,而是更不起眼的小苔藓——装进随身携带的瓶子里。攒了好几瓶,做成标本。更小的时候,他就喜欢待在石头堆里,煤堆里,一待几个小时,寻找自己喜欢的小石头或化石,带回家收藏起来。中考前的年,百武彗星和海尔-波普彗星“光顾地球”。张超怎么都没看到百武彗星,但印象中的海尔-波普彗星特别明亮。他用小本子画下了自己看见的海尔-波普彗星的好几种形态的样子。高中时,父母送了他一台天文望远镜,相对当时的工资是非常奢侈的消费了,虽然和现在使用的望远镜比起来,它就像是一个玩具。但张超很珍惜地使用它,也会用专门的笔记本画下自己观测到的星象。“但我的兴趣真的还是在生物学。只是大学时知道,我考不上生物系了,只好去学了天文。”天文学系是北师大理科类录取分数最低的院系之一。没能做微生物研究的张超进入天文学系,开始了“痛苦”的大学生活。——一进学校就是铺天盖地的数学和物理课。大二大三终于有天文课,发现天文课也听不懂。张超记得,同寝室有外地来的同学,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每天翘课待在寝室打游戏,但期末考试时分数比他还高。对方表示,答题还是用的高中时掌握的方法。现实生活中,当然不存在“考上大学就一切都好了”这样的事情。有人幸运地在大学就遇到了喜欢也擅长的事,也有人像高中一样,为了不挂科而努力。面对痛苦和压抑,能够做的只有忍耐,在忍耐中尽力发现有趣的事。张超参加了天文相关的社团,“当了副社长”。社团活动很有趣,带社员们去密云观星,拍双子座流星雨,半夜冻得瑟瑟发抖熬姜糖水。只是“好玩和学习,是两件事情”。感觉到学业压抑时,也会去旁听生物系的课程,了解了解动物和植物,“这可太简单了”。大四时,也终于有了一些实践类的课程。找不到工作,没保送上想学方向的研究生,“别的专业也不会啊”,只能继续考天文学系的研究生。说着自己是“学渣”的张超,四年间还是努力地学习了每一门专业课,没有挂科,保持着中等的成绩,顺利考上了研究生。大四,考上研究生还没毕业的那段时间,张超买了两台胶片相机,开始漫无目的,或者说有目的地拍摄照片。研究生的时间,一年有大半年都是待在山里的天文观测站。程序设置好,望远镜开始自动观测后,张超会打开随身带的电脑,写一些文章。天文观测站的漫长夜晚就是这样度过的。也是在这样日复一日观测星空时,他感受到,那些星星就在那里,那么遥远,是“永远也够不到的”。但身边也有许许多多值得观察与记录的存在。闲暇时间写的科普文章,关于天文的,或关于动植物的科普小文章,是贫穷的研究生外快稿费的来源,也成为他研究生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契机——在《博物》杂志当编辑与作者。给14岁的孩子们一些建议吧《博物》杂志的工作模式,是编辑需要和作者一起实地考察、完成稿件。去新疆、广西、内蒙、重庆、东北,天南海北跟着作者跑,策划完成选题。为了拍一张古观象台的照片,需要从下午四点进到观象台,待在里面等到晚上关门,天也黑了,晚饭也吃不上,才能拍出想要的。每一张刊登在杂志上的照片,背后都是这样的努力。工作后,张超将他的生活按五年划分成一个阶段。“如果你真的有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两年可以到小成,而五年可以大成。前提是,你真的寻找到一个冷门的小领域。如果这个冷门小领域恰好又是你很喜欢的,那你就一定要坚持做下去。”在《博物》工作五年后,他到了国家天文台的《国家天文杂志》。对现在的他来说,“显微摄影”,那些关于雪花和沙尘的照片,也已经是上一个阶段的痴迷。就像是攀过了一个山头之后,自然就看见了下一阶段的风景。做显微摄影的人越来越多,张超就自然地离开这个已经形成的“圈子”,探寻下一件有趣的事,继续扎进其中。在当下这五年里,他还是带着小朋友办活动,天文观测,写科普文章。工作之外的一大摸鱼乐趣则是“捡破烂”——在国内外拍卖二手网站上寻觅各类古董,譬如古星图。买东西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搞清楚自己买的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来历。在老北京话里,这个叫“喝杂银儿”。“我喜欢每天有惊喜的状态,知道自己肯定能获得新的信息。很多人的工作和喜好可能不是一回事儿,但我的工作就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且这种喜好没有因为工作而减少,反而因为工作在增加。”但回想起工作之前面对学习与考试的时光,张超还是不停地说:“实在是太痛苦了。”发烧还不得不参加考试,不能逃课,不能和老师过不去。但忍耐着,忍耐着,在沙漠里也能找到其他人都忽视的小花。他觉得,如果一个孩子对真实的世界没有兴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电子产品最可怕的地方,是它在破坏孩子对真实的现实世界的乐趣。”张超现在是一个小学生的爸爸,他也带孩子看月看星,识画辨虫,但孩子更有自己喜欢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ijiuhuaa.com/pjhyc/10728.html
- 上一篇文章: 啤酒节复古啤酒大作战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