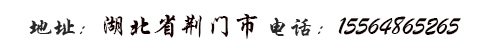葎草丨作为药引子的拉拉藤
|
北京专业雀斑医院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713676953228046314&wfr=spider&for=pc 上篇文章我们写到乌蔹莓,《诗经·唐风·葛生》中的蔓草,背后连接着一个凄美的故事。在《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这两部集大成的著作中,乌蔹莓之后紧挨着的,是另外一种常见的藤本——葎草(Humulusscandens)。 ↑《本草图谱》.卷05至96.岩崎灌园著 ↑野外乱糟糟的葎草丛 byDalgial,fromWikimediaCommons 桑科葎草属的葎草与乌蔹莓生境相同,在野外极有可能看见二者生于一处,这或许是本草学家将它们放在一起的原因。 葎草最大的特点是它的茎、枝和叶柄上都有倒钩的小刺,如果被刮伤,会留下一道疤,疼中带痒。由于它“善勒人肤”,因而在中医古籍中又名勒草、葛勒蔓等。今江浙地区呼为拉拉藤,川赣等地称之为锯锯藤,在我国除新疆、青海外的南北各省区均有分布。 ↑不起眼,但“杀伤力”惊人的倒刺 byChrisEvans,UniversityofIllinois,Bugwood.org ↑《本草图谱》中的精细描绘 如此不友好的葎草,在饥荒年间也是果腹的野草之一。《救荒本草》中载有具体的做法,在书中它的名子叫葛勒子秧:“采嫩苗叶煠熟,换水浸去苦味,淘洗,油盐调食。”果然,它的味道是苦的,吃之前需反复淘洗,最后还得用油盐调食。不过古时候人们吃它完全是因为荒年间食物不足,现在估计是没有人采它当野菜的。 我之所以认识它,是因为中学时患急性肾炎,吃过的中药里就有它。医院住院,两周回家后复发,父亲医院抓药,吃了半个月并不见好,听说姑妈村里有偏方,就想带着我去试试。那家的小女儿在也曾患有同样的病症,多年前在老中医处得了一副药方,数个疗程后即见痊愈。彼时老中医已不在世,但药方那人还保留着,病例和化验单据也都留着,虽然字迹已模糊不清。那中年男人也是个老实的农人,他从存放粮食的屋子里挪出一个蛇皮袋,拿出几包枯草,用白色的塑料袋装着,对父亲说袋中的配方,与她女儿服用的一模一样,但还需要找一味药来做药引子。 多日求医未果,父亲已是忧心忡忡,但那日父亲看了病例和化验单据,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急切地问这药引子是什么,是否难找。那人把我们引到屋外,指着门口一堆青绿的藤蔓说,喏,就是这种浑身带刺的野藤,到处都是。后来我才知道,它的名字,就是葎草。 按照那人给的偏方,一个疗程后,却丝毫不见起色。父亲有些怀疑,担心是不是给的药钱不够多,对方是不是还留了一手。再次去的时候,父亲拎了两瓶白酒,一条香烟,嘱咐他一定要给足药量。于是我们又带着同样的几包草药回家,父亲又去园子里砍了一些葎草回来同煮,医院复查,依然不见效。这时父亲就急了,说这什么鬼偏方,再不信! 事后回忆,其实这偏方有很多可疑之处,例如,肾炎患者需禁吃或吃少量的盐,但那人却告诉我们不必禁盐;肾炎患者需多吃西瓜这样水分充足的水果以利尿,结果那人却说要禁吃西瓜这类含糖较多的水果。总而言之就是,不禁盐,反禁糖。每每想到此,父亲不禁懊恼且愤懑:“怎么会相信这种违背常识的荒谬之言?差点误了我儿的病!”父亲也是着急,所谓病急乱投医。 ↑葎草雄花 我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那浑身带刺的藤子是什么鬼,竟然还用来做药引子?谁知,记载中,葎草竟然还真的有利尿之功效: 《唐本草》:“葎草味甘、苦、寒,无毒。主五淋,利小便,止水痢,除疟虚热渴。煮汁及生汁服之。生故墟道旁。”[1] 其实,抛开药效不论,葎草的用处也大着呢。其茎皮纤维可作造纸的原料,种子油可制肥皂,果穗还可代啤酒花[2]。中国植物志上,桑科葎草属下的植物仅三种,另外两种之一就是啤酒花(Humuluslupulus),为酿造啤酒不必可少的原料。(啤酒花 啤酒的灵魂) ↑葎草雌花序可代替啤酒花使用 借着葎草,我终于写到父亲带着我四处求医问药的日子。那段误诊的经历,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后来父亲毅医院,去找正宗的大夫,带着我辗转家里,医院和学校;每周医院复查、抓药,回到家熬药、装瓶,傍晚又骑着摩托送药和饼干到教室门口。如此两年,风雨无阻,一直到初三中考,方才痊愈。十五岁那年治好病,是我们父子俩度过的第一个难关。 我总记得一个场景。有一次复查,医院附近吃炒面,那炒面特别好吃,吃完我问父亲能不能再要一碗。父亲突然非常高兴,冲老板大喊:“再来一碗!”也许父亲觉得,我的胃口好了,说明身体是真的终于有了好转。 [1](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中华书局,年,第页。 [2]《中国植物志·葎草》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ijiuhuaa.com/pjhzzz/10670.html
- 上一篇文章: 第31类饲料种籽
- 下一篇文章: 螃蟹免费吃全场精酿啤酒7折玉门继成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