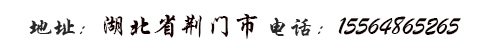诱我深入连载丨我家新橙
|
点击上方↑↑↑蓝字 她不吭声了,他也没追着问。对傅棠舟来说,这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插曲,可对她而言,或许会在暗中改变什么东西。至于为什么,她心知肚明。她和傅棠舟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大到外人很难相信她是因为爱他才愿意待在他的身边的。成年人的世界里,用钱能买来的都不必交付真心,而她这样的年轻女孩往往最容易用钱搞定。有时候就连顾新橙自己也不敢相信,她和傅棠舟真的是在谈恋爱吗?正因为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存在,她从未和身边的人提过他的名字。不匹配的爱情在外人面前给她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羞耻。至于私底下,傅棠舟对她倒是也存了一颗温柔心。只要她提要求,他都会满足——可她要是不说,他也很少管。她不知道他是天生如此还是只对她这样。事实上,傅棠舟没问过她以往的情史,顾新橙也没打听过他的。他大概觉得校园恋爱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不值一提,所以懒得问。而顾新橙是不想问,谁愿意没事找事,给自己找不痛快呢?就算问了,他八成也不会跟她说。傅棠舟把车开到三里屯一家商场的地下停车场里。她打开安全带,刚想下车,却被他拉住了。修长的手指握住她细细的一截手腕,他将她整个人拽到怀里。顾新橙的脸颊贴着他的胸膛,她听到他的心脏有力的跳动声,那心跳声一下一下叩击着她的心扉。傅棠舟绷着脸,口吻倨傲又冷淡:“规则和话语权都掌握在强者手里,要么服从,要么就变得比他更强。”顾新橙愣怔,一时没明白他究竟是指行业潜规则还是别的什么。在这种事上,傅棠舟总是以上位者的姿态发号施令。他确实有这个实力。一个人说的话对错与否,有时并不是看他说得有没有道理,而是看他的身份够不够格。市面上各类成功人士的心灵鸡汤被宣传得风生水起,不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吗?如果只是无名小卒,大道理讲得再漂亮,也很难获得喝彩。傅棠舟托着她的下巴,一个带着侵略气息的吻落了下来。顾新橙被动地仰着头承受着,心底如小鹿乱窜。因紧张而不安的手轻轻推搡着他,“不能在这儿……”她想不通傅棠舟是哪门子心血来潮,要在这车来车往的地下停车场跟她亲热。傅棠舟抵着她的额头低声询问:“在这儿什么?”她的眼底浮着一点儿水汽。她咬着唇不肯说。他的嘴角噙着一丝笑意,拇指指腹擦过她胭红的下唇。他逗她说:“亲也不让亲了?”他说得好像是顾新橙想多了一样。她有点儿恼,眼神飘忽地扫过他那里。这能怪她多想吗?她腹诽着。傅棠舟将她的一缕长发勾回耳后,另一只手松开安全带,腰腹微微耸动一下——这下他终于能活动了。顾新橙眨眨眼,以为他真要在这儿跟她亲热,登时警铃大作。谁知他拍拍她的脸颊,低声说:“乖,让让。我要下车。”顾新橙:“……”俗话说,先撩者贱。可这在他们之间不成立。每一次顾新橙都被他压制得死死的,根本斗不过他。顾新橙下车的时候,脑子里忽然浮现出一句话:“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几千年前老祖宗就告诫过女孩子不要沉溺于男女情爱,结果她遇到傅棠舟后还是陷了进去,拔也拔不出来。两人去了三里屯的一家日料馆吃晚餐。这家餐厅今年刚被米其林评上星,得提前很久预订才有位置。 餐厅的环境和地段都没得挑,菜式以正宗日式寿喜锅闻名,食材均是当天从日本空运来的。与这样高档的服务相对应的,自然是超乎寻常的昂贵价格。顾新橙翻了两页菜单,表面上装作波澜不惊,内心实则惊涛骇浪。她实在没法儿说服自己一小份鱼子酱卖四五千是一个合理的价位,要是用她妈妈的话说,这就是洗干净脖子等着人来宰。然而,天底下真有这种人。傅棠舟轻轻叩了下桌子,指着那一页对服务员说:“来两份。” 顾新橙立刻说:“我不吃。”傅棠舟:“不爱吃?”顾新橙:“……”哪里轮得到她说爱吃不爱吃?她压根没吃过这玩意儿。她点了几个还算物美价廉的手作寿司之后就不再碰菜单了。傅棠舟让人直接下单了两份鱼子酱。这鱼子酱颗粒饱满圆润,还泛着微微的金色光泽,显然是上品。顾新橙捏着贝壳勺,犹豫好久也没动。傅棠舟吃得倒是从容淡定。她将自己的这份鱼子酱推到傅棠舟面前:“你吃。”“给你点的。”“我怕。”这像青蛙卵一样颗粒密集的鱼子酱令她头皮发麻。她小时候被青蛙吓过,对和青蛙有关的一切都有着深深的恐惧。后来她读了莫言的《蛙》,才知道这世界上有蛙类恐惧症一说,而她一定是资深患者。傅棠舟说:“这是鱼卵。”顾新橙深吸一口气,摇了摇头,坚决不肯尝试。“胆子那么小呢?”“有些事情可能一辈子都没法儿克服。”这不是多一些勇气就能跨越的,那种恐惧已经深入骨髓。顾新橙的胃口不大,她吃了几块牛肉和几个寿司就饱了。吃完饭,傅棠舟说:“等会儿陪我去趟酒吧。”顾新橙正用餐巾拭口,闻言一顿。“一哥们儿的酒吧刚开业,去捧个场。”“要不要准备礼物?”“什么礼物?”“两手空空地过去不合适吧?”傅棠舟笑着说:“我不是带你过去吗?”顾新橙默默地将餐巾放到一边,瓷杯中的抹茶沉淀到了杯底,清澈的茶水浮在杯中,空气里平添了一丝微妙的气氛。傅棠舟起身,漫不经心地又说了一句:“我让人抬了架钢琴过去。”“哦。”她闷闷地应了一声,没再多说。两人一前一后走到餐厅楼下,寒意扑面而来。傅棠舟忽然顿住脚步。顾新橙显然有心事,差点儿直接撞到他的后背上。她抚了一下胸口。他却凑近了,冷不丁地说道:“我刚刚是开玩笑的。”顾新橙低下头,心想他是不是太过敏感了。她知道只是一句玩笑话啊。可是,如果他在意她,为什么要说她是他带去的礼物?她明明是一个鲜活的人啊。顾新橙跟在傅棠舟的身后,他正在和朋友打电话确认酒吧的具体地址。三里屯附近使馆众多,这里有北京著名的酒吧街,晚上能看见不少外国人。顾新橙在灯红酒绿的街道中穿行,耳边传来一个轻浮的口哨声。她侧目一瞧,两个黑人老外正冲她不怀好意地笑着,两口白牙格外扎眼。她心底一阵发毛,三步并作两步地追上傅棠舟,走到他的身边。傅棠舟挂了电话,见她瓷白的脸上神色惊惶,于是问:“怎么了?”顾新橙吸了下鼻翼,闷声说:“冷。”他勾勾唇,然后说:“你不是说你们南方人挺扛冻吗?”她杏眸微闪。他把胳膊忽地搭到她的肩上,将她搂入怀中,然后说:“怕冷就靠近点儿。”她贴着他的黑色风衣,鼻尖萦绕着清冽的雪松香气。一星半点儿的男士烟草香混杂于其中,味道极淡。街边的棉花糖机在吆喝声中拉扯出粉红色的糖丝,那糖丝一缕一缕地缠绕成云朵般松软的草莓棉花糖。顾新橙的嘴角不经意间漾开一抹浅笑,她决定将方才所有的不愉快抛诸脑后。这家酒吧名叫零下七度,选址不错,是人流量最密集的地段。一进门,顾新橙就被五光十色的灯球闪花了眼,强大的音浪更是震得她的耳膜发疼。舞池里,一堆男男女女正在疯狂地摇摆,俨然一副群魔乱舞的场景。傅棠舟带着她上了二楼,罗马柱旁摆了一架三角斯坦威,底下还铺了红毯。这么高雅的钢琴和这酒吧的氛围格格不入。他走上前去掀开钢琴盖,然后说:“你来试试。”顾新橙略窘:“我好久没练过琴了。”以前她在家的时候还能练练琴,上大学以后想练琴还得去学校附近的琴室。她嫌麻烦,渐渐地也就很少去了。她不是一个对音乐有着执着追求的人,弹钢琴不过是家里人从小给她培养的一项特长罢了。然而,就像会游泳的人碰到水、会骑自行车的人碰到自行车一样,会弹钢琴的人一碰到钢琴,手指的记忆也会跟着被唤醒。顾新橙的指尖碰上如水般冰凉丝滑的琴键,立刻弹出了一串音符。这钢琴的音色绝佳,如琅琅环佩相撞,对得起它不菲的身价。傅棠舟单手撑在琴边,微微弓下腰,凑到她的身旁:“你弹的什么?” 顾新橙嫩葱般的纤手顿住了:“《梦中的婚礼》。”他握住她的手说:“怎么弹的?教教我。”他的手指骨节分明,手腕处的一粒铂金袖扣泛着柔和的光泽。浮动的气息拂过顾新橙的发侧,她稍稍转过头,见他根根分明的睫毛在眼底落下一层薄影。他总能不动声色地把她撩拨得心神不宁。顾新橙正苦思冥想着如何跟他讲解,身后忽然响起一阵爽朗的笑声:“我说傅哥怎么还没到?原来是忙着陪美人啊。”她心下一惊,立刻把手抽了回来。傅棠舟从容不迫地站直了身子,顾新橙这才瞧见来人。那是个二十多岁的英俊男人,头发挑染了一缕金色,耳垂上缀着一枚银色的耳钉,穿的是欧美潮牌。“哟,钢琴弹得那么好,音乐学院的吧?”他笑得玩世不恭,“这钢琴给我可是白瞎了,也就当个摆设,还得你这样儿的人来弹才好。”这恭维话说得顾新橙挺不好意思的,就她这三脚猫的水平,怎么可能是音乐学院的?“我哥们儿,林云飞。”傅棠舟介绍说,“她叫顾新橙。”顾新橙微笑,然后说:“你好。”林云飞咧着嘴巴笑:“哦,原来是顾妹妹。”这声“妹妹”叫得亲昵,顾新橙有点儿不适应。傅棠舟:“你小子这便宜占得忒(太)溜。”他一开京腔打趣,顾新橙就知道这林云飞和他关系不浅。他平日里不常开京腔,也就是遇到熟人才会说上一说。林云飞嘴贫道:“不叫妹妹,难道叫姐姐?那我不把人姑娘得罪了?”顾新橙说:“叫名字就好。”林云飞应得麻利:“哎,知道了,顾妹妹。”顾新橙懒得跟他计较称呼,既然他是傅棠舟的朋友,想必也不是什么坏人……吧?“傅哥,进去玩玩呗。”林云飞说,“你这大忙人难得来一趟,回头可别怨我招待不周啊。”傅棠舟用胳膊碰了下顾新橙,然后说:“走,过去坐坐。”顾新橙跟着他进了包间,一推门,就见点歌机旁坐了个男的。他正拿着话筒鬼哭狼嚎地嘶吼着:“死了都要爱——”“爱”字喊到一半,他就哑火了,只因瞥见了傅棠舟。坐在沙发上调笑的男男女女一愣神,纷纷往边上挪动,于是正中间空出一人的位置。傅棠舟若无其事地往那儿一坐,轻轻拍了下腿,对顾新橙说:“过来。”那些人这才注意到他还带了个姑娘,这姑娘的相貌是一等一的好。她文文静静、眉眼温柔,身上蕴藏着一种独属于江南水乡的味道。顾新橙走近了才发现没位置留给她。她心想,这坐哪儿?他的腿上?傅棠舟用目光扫了一眼身旁的女人。那女人立刻站起来,坐到了沙发的最边上。顾新橙抚了下裙子,僵直着脊背坐下,只挨着一点点儿沙发。她极少来这种场合,并不能做到像傅棠舟那样泰然自若。林云飞及时出来活跃气氛:“今儿个傅哥过来,大家可劲儿喝,都记他的账上。”林云飞不拿傅棠舟当外人,这种事都能做主。关键是他说了之后傅棠舟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并不恼火。场子又热闹起来。顾新橙好奇地问:“他是谁啊?”傅棠舟倒了杯啤酒,随口说:“京城一小开。”这显然不是顾新橙想知道的答案。傅棠舟抿了一口啤酒花,补充道:“我妈亲戚家一孩子,跟我喊声哥。”得知林云飞和傅棠舟沾亲带故,顾新橙懂了。难怪他能在这么好的地段开这么大一间酒吧,原来并不稀奇。林云飞拿了骰子过来:“傅哥,别光喝酒啊,跟大家伙儿玩玩。”傅棠舟指了指顾新橙:“她的手气比我好。”顾新橙扯了下傅棠舟的袖子,小声嘀咕一句:“输了要喝酒呢。”“别输不就行了?”“玩骰子和玩牌不一样的。”她玩牌的时候既会记牌又会算牌,一般人真玩不过她。可玩骰子全靠运气,她并没有自信保证能赢。傅棠舟把她面前的酒杯斟满,然后说:“你输了,我替你喝。”林云飞笑笑:“还是傅哥会心疼人,顾妹妹就别谦虚了,来吧。”他们玩的是最简单的比大小,六颗骰子一起摇,谁点数最小谁就喝酒。顾新橙事先猜想得不错,这游戏跟玩牌有天壤之别。她甚至怀疑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力气小,所以每次摇出来的点数也很小。傅棠舟在众人的起哄声中将杯中的啤酒一饮而尽,这是第六杯了。他放下酒杯,用手臂揽着她的细腰,在她的耳边低语:“你趁机报仇呢?”顾新橙脸一热,扭捏地推开他,然后说:“我去趟洗手间。”林云飞哈哈大笑:“要去也得是傅哥去吧?”顾新橙像是做了错事一样落荒而逃。进了洗手间,门一落锁,她总算缓了口气儿——她果然不太适合这种场合。正巧趁这工夫看一眼手机,她在隔间里回了几条 “无锡。”“江浙一带的呀,沈阿姨算起来也算半个江浙人呢。”“沈阿姨?”“就是傅哥他妈,海军大院儿那片儿好多都是江浙过来的。” 傅棠舟没跟她提过他的家人,她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妈妈姓沈。出于某种心理,顾新橙试探着问了一句:“他的妈妈……是什么样的人?”“沈阿姨这人吧……”林云飞欲言又止,把皮球踢给了傅棠舟,“你直接问傅哥不就完事儿了?”顾新橙望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路灯,半晌没接话。车内沉默的气氛没有持续多久,林云飞就熟练地开启了下一个话题:“顾妹妹,你什么专业的啊?”他这人说话做事大大咧咧、直来直去,不像顾新橙那样有万千思绪,斩不断理还乱。“金融。”“这专业好啊,赚钱。”“没你开酒吧赚钱。”“唉,可别提我这酒吧了,也就看着赚钱,刚一开业就巨亏。”林云飞像是有说不完的话似的向顾新橙抱怨着他这酒吧哪儿哪儿亏钱。顾新橙安安静静地听他嘚啵嘚啵地往外倒苦水,然后随口说了一句:“这个查查酒水盘点表就清楚了。”“酒水盘点表是什么?”难怪酒吧会亏钱,酒水是酒吧最重要的存货,老板竟然连个明细账都没有。“就是一张表,上面记录着每一样酒水的库存量、销量、进货量。每天盘点一次酒水数目,这样不容易出错。”“还是顾妹妹厉害,我傅哥的眼光真好。”林云飞眉开眼笑,“能不能劳烦顾妹妹帮我做一张表,我们吧台卖酒的小妹哪懂这个?”他倒是挺自来熟。“网上一搜就有了。”“网上搜来的哪有顾妹妹弄的好?万一哪儿错了我也看不出来啊。”林云飞又说,“顾妹妹你帮帮我,我不会让你白忙活的。”顾新橙拧不过他,只好应了。说话间,他不知不觉开到了五道口。她望着窗外熟悉的街景:“前面那个路口停下就好了。”林云飞看了一眼导航:“离A大不是还有段路吗?”“我自己走回去就行。”林云飞靠边停车。顾新橙打开车门,说了一句谢谢。“路上小心,可别忘了我那表啊。”林云飞叮嘱一句,关上车窗离开了。 购买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ijiuhuaa.com/pjhzzz/10678.html
- 上一篇文章: 螃蟹免费吃全场精酿啤酒7折玉门继成酒
- 下一篇文章: 资本市场强势切入精酿啤酒已有企业获千万